读《梦幻花》的过程中,我反复意识到一种难以忽略的不安。这种感觉并不是来自悬疑结构本身,也不是因为故事节奏或逻辑漏洞,而是一种更隐约、却持续存在的阅读体验:女性角色似乎总是以“被看见”的方式进入叙事,而不是作为一个正在行动、正在思考的人出现。她们并非被粗暴对待,语言也称不上低俗,但正是这种“看似温和”的描写,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。
在小说中,女性角色初次出现时,叙事往往优先交代的是她们的外表。穿着、身形、身体线条、给他人带来的视觉印象,构成了她们被引入故事的主要方式。类似“穿着T恤和短裤”“腿部线条显眼”这样的描写,本身并不激烈,却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角色定位:她首先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,其次才可能是一个人物。这种顺序并非偶然,而是反复出现的叙事习惯。
问题并不在于文学是否可以描写外貌,而在于女性角色的外貌被反复置于叙事中心,而她们的内在经验却被弱化甚至忽略。与之相对的是,男性角色通常拥有完整的心理描写和行动轨迹。他们的犹豫、选择、信念与转变,构成了故事真正向前推进的动力。女性角色更多承担的,是触发这些变化的功能:她们的存在让男性角色产生情绪、回忆或行动冲动,却很少被允许拥有同等重量的叙事空间。
这种书写方式往往被解释为“自然”“青春”“细腻”,也正因为如此,它很少被质疑。男性的凝视被当作一种无需反思的感受,被包装成心动、悸动或纯真的回忆,而女性是否意识到这种凝视、是否感到舒适,往往并不重要。叙事默认读者会站在观看的一侧,而不是被观看的一侧。当这种默认立场没有被点破,它就显得理所当然。
但对于不少女性读者而言,这样的描写很难完全无感地接受。阅读时产生的不适,往往不是因为某一句话“过分”,而是因为一种熟悉的结构被再次复制:女性的身体先于她的意志被呈现,她的存在被简化为一种视觉经验,而她是否愿意、是否自觉,却并不构成叙事的一部分。这种不适并不是敏感或过度解读,而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经验的直觉反应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问题并非东野圭吾个人独有。它更像是一种被长期正常化的文学传统,尤其在通俗文学与悬疑小说中,男性视角常被视为“中性视角”,而女性则被当作安全的审美对象。这种结构使得女性被描写、被观看、被评价,成为一种无需解释的叙事前提。当这种前提不被挑战,它就会不断被复制,甚至被奖项和市场反复肯定。
也正因为如此,对《梦幻花》的这种批评并不是否定作品的完成度,更不是否认其他读者的阅读体验。它只是试图指出,在技巧成熟、结构稳妥的叙事背后,是否仍然存在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、却并不公平的观看方式。当文学不断重复同一种视角时,被压缩的不只是女性角色的复杂性,也包括读者理解世界的可能性。
提出这样的疑问,并不是要求文学承担道德说教的功能,而是希望阅读本身能够多一点自觉。文学并不只是讲故事,它也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他人、如何理解关系。当女性始终以“被看见的身体”进入叙事时,这种看似无害的描写,实际上正在悄悄限定她们可以被理解的方式。
或许,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“这样的描写是否允许存在”,而是:当我们一次次称赞作品的真实与细腻时,是否也愿意停下来想一想,它究竟真实地站在了谁的视角中,又忽略了谁的感受。阅读并不会因为这样的追问而变得狭隘,相反,它可能因此变得更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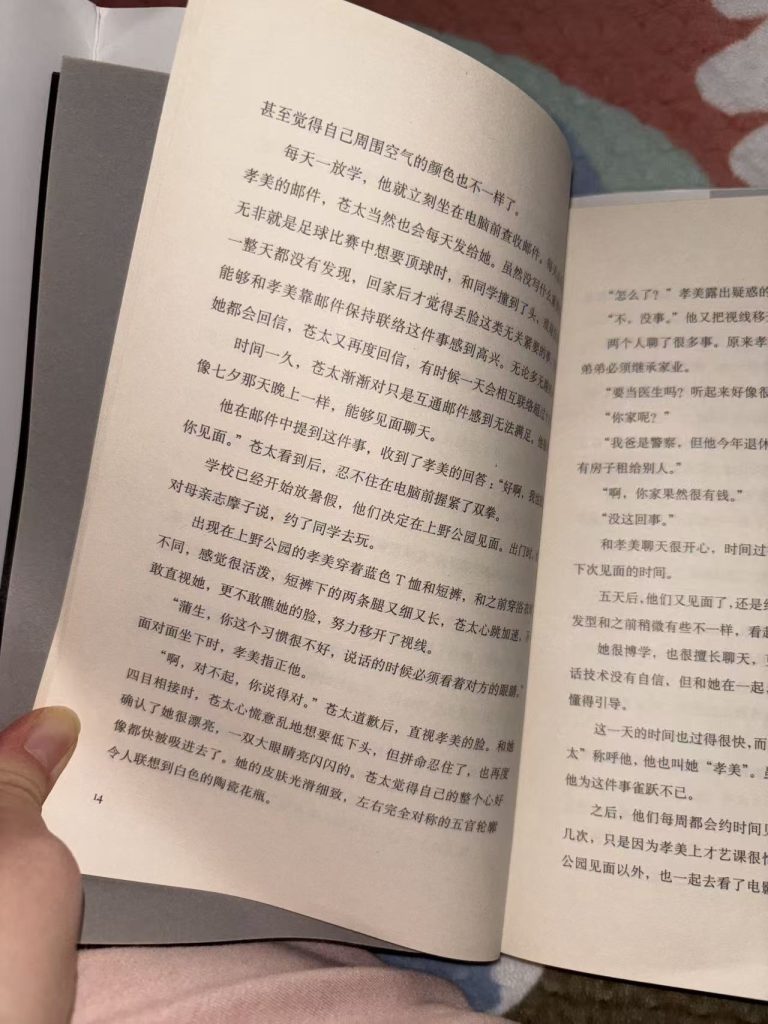
本文作者为菊,转载请注明。